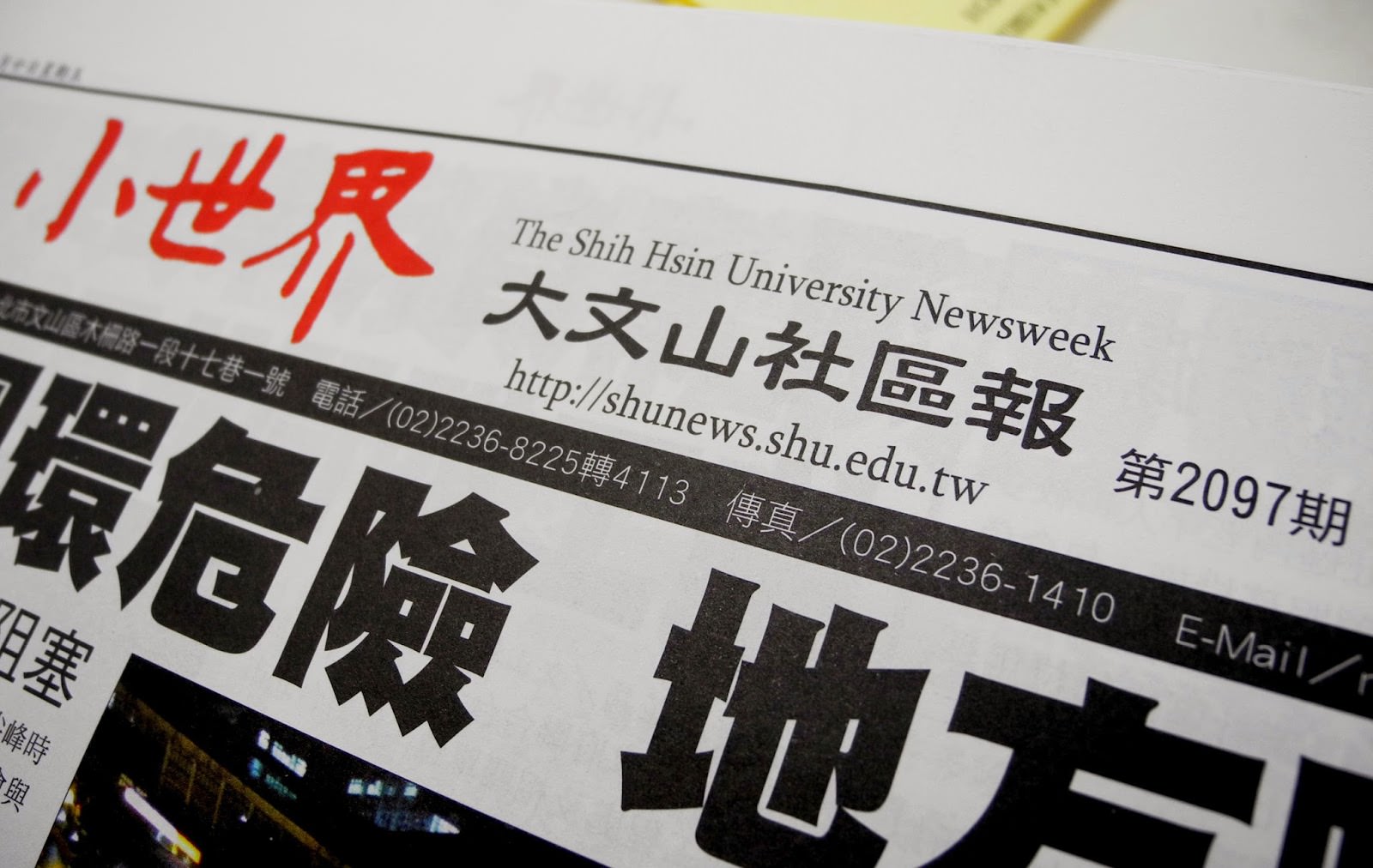“我从国中的时候因为看了一些书,那时就决定未来想当记者,所以新闻系是必然的,来台湾可能是巧合。”世新大学新闻学系的傅心怡很早就立下自己的理想,也累积了相当积极的实战经验,大三曾担任小世界电视组的总编辑,上学期在公共电视新闻实习,这学期则在香港卫视实习,时常出入立法院采访台湾的政治新闻。
高考前刚好看到报纸上有招生的讯息,跟家人商量过后觉得可以报报看,当时还在等第二批填志愿的时候,就被通知录取世新大学,因为也不想继续为了要念哪所大学而烦恼下去,便决定来台湾了。“因为资讯比较匮乏,周边的人可能对台湾不太了解,我刚来的时候就觉得台湾满神祕的,也像大部分刚上大学的新鲜人一样兴奋的心情吧!”
好像不是我以为的民主
“我大一的时候还满爱念书,原本来台湾之前有看过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纪录片,后来发现图书馆有一面书柜都是六四天安门的书,这么多以前看不到的资讯,我就把它们全部都看完了!”另外她也会读一些跟性别议题有关的书,未来如果要读研究所,可能考虑性别研究这块领域。
她曾观察到性别意识在媒体圈吊诡的现象,“别人叫我女记者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人去讲‘男记者’?总是要刻意强化一些刻板印象,像是女司机、女强人啦…..,比如报导会写说‘女司机导致车祸’,我心想难道男司机就不会导致车祸了吗?”
“刚来台湾那一年碰到选举,见识到蓝绿之间打起来、谩骂还满恐怖的,但同学之间就算政治立场不一样,还是可以打屁聊天,或是互相拿身分开玩笑,其实相处还算融洽的。”不过谈到318占领立院的社会运动那期间,她曾看到脸书上一些比较要好的朋友会直接写说“该死的中国人”、“支那”之类的话,让她看了很难过,明明平时见面的时候都还好好的。“不过见面的时候好像也不太聊到,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来上课,都去青岛东路了吧!”傅心怡笑说。
“那时候我当电视组总编辑,学校当时为了保护学生和器材,怕学生以媒体身份进去有危险,便说电视组不能发太阳花议题。”她回忆当时只去过抗争现场两次,心怡自嘲说:“我应该是走错团了,因为他们都是在骂中国人,可能是我一开始进去的位置比较不对吧,没有上到街头的课,刚好被我看到了比较恐怖的一面……”当时她见到许多从中南部翘课连夜上来的国中学生纷纷上台说自己的看法,台下就只是跟着大声起哄说“好!”,让她难以苟同这种凑热闹的现象,“好像不是我以为民主的感觉。”
比起撤稿感想,事件经过更重要
前年底因为教育部公布“常态性学杂费调整方案”草案,拟放宽私立大学学费调涨5%、国立大学10%,引起大学串连抗议不合理涨学费,当时傅心怡采访世新劳权小组在舍我纪念雕像前的“我要说话:反涨学费”公听会,为了平衡报导立场,也有去访问校方,但直至截稿前都没有接到回应。
原先排版的时候,这份报导被排进头版,指导老师也读过了,“没想到系主任胡光夏下来看之后说那则不能放,对我来说是非常突然地被撤稿了。”当时不少人想采访她被撤稿的感想,但因为她不是编辑并不在现场,“我没有答应采访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过程也是别人转述给我的,我只能说我被撤稿的感想,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好说的,他们更应该了解的是事件的经过。”
当校园报只剩艺文版,学生还能知道什么?
毕竟世新大学是传播界人才的重点培育基地,撤稿的争议很快就被传开了。后来在102学年度下学期小世界报纸组实习手册中,原本“版面规画”对于五版“世新最前线”的内容规画,从“世新行政、社团等校园新闻”,改为“世新大学艺文、社团活动之校园新闻”。原本可以报导学校发生什么事或议题,“后来变成是艺文版,就发一些可能谁今天来学校或是活动宣传之类的。”傅心怡曾在脸书动态上感慨“只是觉得,若小世界真的不存在校园版了,或存在的只是校园艺文版(文山好邻居版),那学生可能再也不会知道,学餐水果来源不明、舍我楼电梯分流、异便当油烟污染⋯⋯”
聊到她目前在香港卫视的实习工作,我好奇陆生无法在台打工的问题,她澄清目前实习是没有薪水的,“原先想实习是因为以为可以因此留在台湾工作,因为香港可能是外资……,但后来发现薪水也是从台湾的户头汇过来的,所以我还是不能借此留在台湾工作。”主要报导台湾的时事新闻,她笑说:“他们应该不知道我是陆生,因为我的实习身分都隐藏在临时采访证了,不过也还好,我也听不到什么国家重大的事情啦!”
在最接近墙的地方,尽最大的努力
比较两岸在新媒体方面的发展,傅心怡认为台湾发展比较蓬勃,“在同一时间点比较,台湾的使用者比率上比较多。在大陆的阅读资讯来源多半还是停留在官方媒体,或是门户比较大的,比如搜狐、腾讯…..,一般民众比较少会去看独立媒体。”原先对台湾媒体的印象,她觉得是很开放、自由的,但后来陆续观察到一些乱象,被撤稿事件之后也让她体悟到媒体受到支配的一面,“被钱、被上级,或组织方面的控制,其实并没有百分百的自由。”
另一方面她感受到自由可能带来的乱象,“前几天有个爸爸把自己儿子杀了,因为儿子患有疾病,儿子也同意爸爸杀了他,当时我看到新闻画面,那个爸爸脸部已经被遮住正在押送途中,记者还在追问说‘你是不是已经不再爱你儿子’之类的这种白痴问题,我就觉得还满过分的。”为了拼命应付长官或画面的需求,而忽略了报导过程中要注意的细节问题。“可能大家新闻做久了,反而无法感同身受。”她接着话锋一转,笑说自己可能也是在讲风凉话,搞不好进了业界也会是如此。
因为来台湾念了四年书,虽然毕业后还没有明确打算,但她期望之后工作地点可以离家近一点,就有比较多时间可以陪家人。目前所受到的新闻专业训练,或是参与过的议题采访工作,被问及是否担心很难在中国有相当自由的发挥空间,透过这些新闻人必经的担忧,她反省道:“你一直去撞墙、撞墙,就慢慢会知道墙的边界在哪里,那我就会是在最靠近墙的地方,就是在体制内尽最大的努力,因为我必须要保住我的饭碗才能一直写下去。”
她也以之前在台湾备受讨论的柴静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为例,“我觉得柴静很聪明,因为现在环保议题大家是最关心的,跟每个人息息相关,又没有这么威胁到政府,才会让议题一被推出来就受到这么多人关注,也是她在离开央视后通过独立媒体可以发挥的影响力。”
“把自己的情感带入报导是新闻学上的问题,但也正是因为跟受访者感同身受,以妈妈的角色诠释雾霾的问题,这是她向来的风格,也因此让很多人关注这个报导。”她认为记者某方面也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因此有自己的观点带入事件很重要,未必是放进日常工作的报导中,可能是发布在自己的平台上。“我觉得记者无论如何,一定要有自己的态度才行,不然的话,很像是这份工作在‘做’你,而不是你在‘做’这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