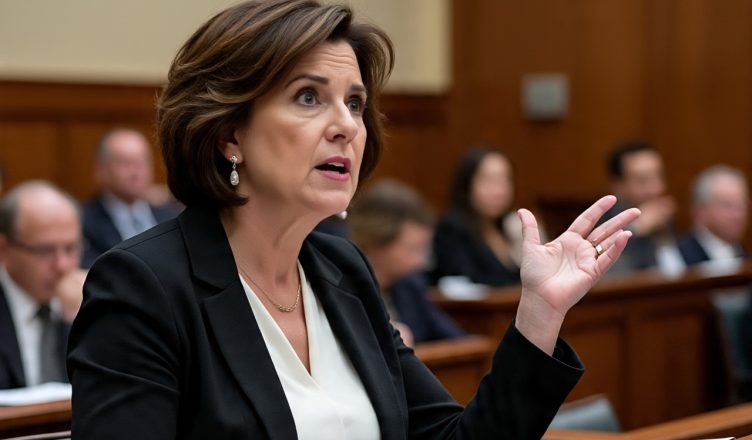文/孙靖洋 (前洛杉矶世界日报采访主任/副总编辑)
2015年夏天,我接到陪审员征召通知,
我参与过本案刑案部分的最前面小一段,当时我在庭上,
我参与过多次陪审员出庭待命候选,最长的是九天,
检辩双方在决定12位正选陪审员、2位备选陪审员之前,
那天我是最后一批被叫进法庭内,接受检辩双方质询的候选人,
由于时间有点久,细节不记得,检察官问我的问题大约是,
但在洛杉矶开车的人都知道,没有人会在65哩的路段开65哩,
检察官的原始动机,我能理解,很可能是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
检察官提出问题后,还絮絮叨叨的讲了一大篇道理,
本人的脾气向来很火爆,在他说完最后一句后,
检辩双方都没有再对我发问,但也没有主动把我踢出去。
当天我离开法庭后,审判程序立刻展开,检辩双方开始开场陈词,
我因为参与过一小段,所以也盯着新闻发展。没想到全案审了几天,
美国有大约八成以上 (具体数字要再查)刑事案件是以认罪协议方式结案,
但吊诡的是,那些开审之后才达成认罪协议的案子,
以该案而言,如果该田径教练如果是清白的,
虽然很多认罪减刑的案件,有法律实务面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