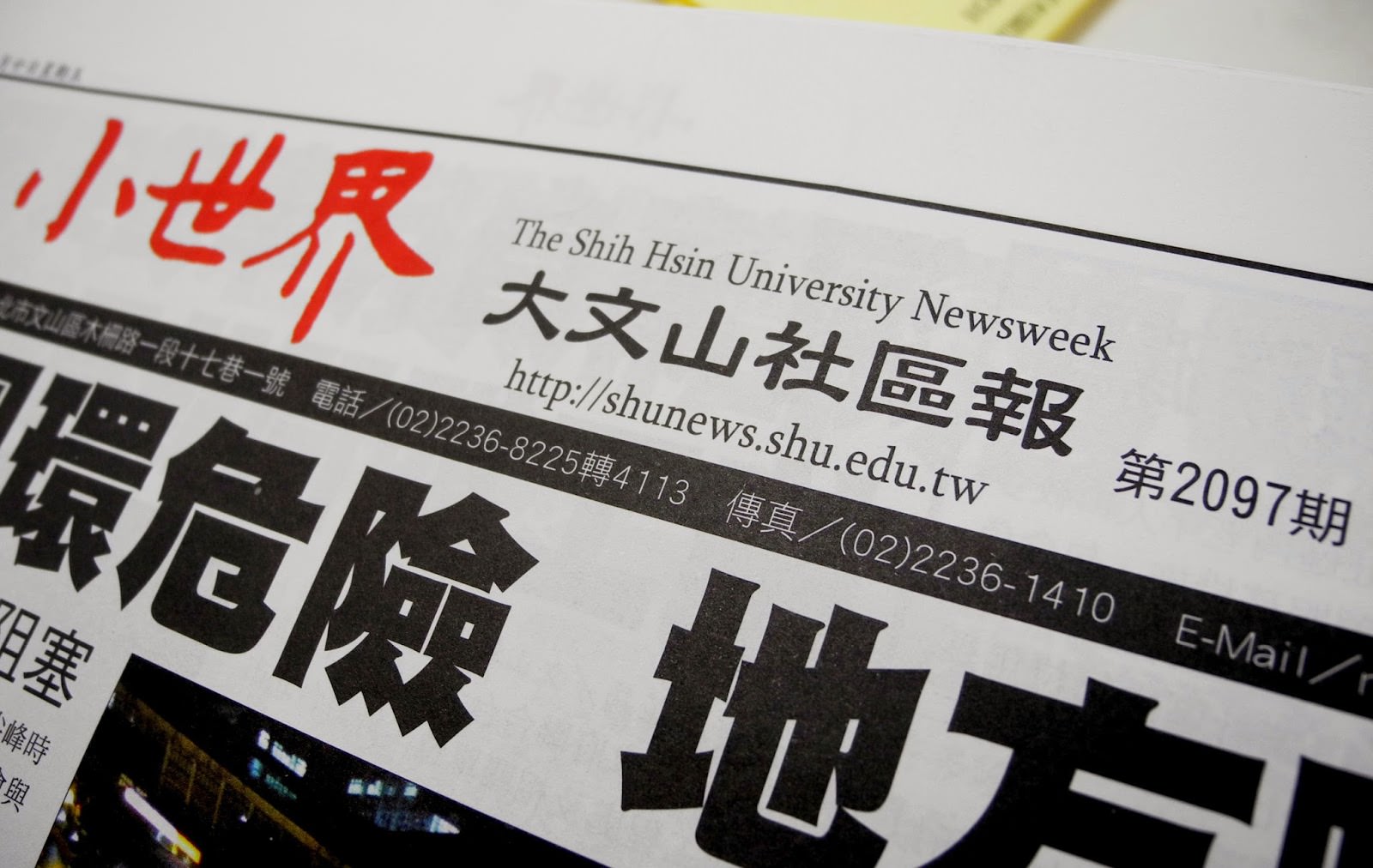「我從國中的時候因為看了一些書,那時就決定未來想當記者,所以新聞系是必然的,來台灣可能是巧合。」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的傅心怡很早就立下自己的理想,也累積了相當積極的實戰經驗,大三曾擔任小世界電視組的總編輯,上學期在公共電視新聞實習,這學期則在香港衛視實習,時常出入立法院採訪台灣的政治新聞。
高考前剛好看到報紙上有招生的訊息,跟家人商量過後覺得可以報報看,當時還在等第二批填志願的時候,就被通知錄取世新大學,因為也不想繼續為了要念哪所大學而煩惱下去,便決定來台灣了。「因為資訊比較匱乏,周邊的人可能對台灣不太了解,我剛來的時候就覺得台灣滿神祕的,也像大部分剛上大學的新鮮人一樣興奮的心情吧!」
好像不是我以為的民主
「我大一的時候還滿愛念書,原本來台灣之前有看過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紀錄片,後來發現圖書館有一面書櫃都是六四天安門的書,這麼多以前看不到的資訊,我就把它們全部都看完了!」另外她也會讀一些跟性別議題有關的書,未來如果要讀研究所,可能考慮性別研究這塊領域。
她曾觀察到性別意識在媒體圈弔詭的現象,「別人叫我女記者的時候,我都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沒人去講『男記者』?總是要刻意強化一些刻板印象,像是女司機、女強人啦…..,比如報導會寫說『女司機導致車禍』,我心想難道男司機就不會導致車禍了嗎?」
「剛來台灣那一年碰到選舉,見識到藍綠之間打起來、謾罵還滿恐怖的,但同學之間就算政治立場不一樣,還是可以打屁聊天,或是互相拿身分開玩笑,其實相處還算融洽的。」不過談到318佔領立院的社會運動那期間,她曾看到臉書上一些比較要好的朋友會直接寫說「該死的中國人」、「支那」之類的話,讓她看了很難過,明明平時見面的時候都還好好的。「不過見面的時候好像也不太聊到,可能是因為他們沒來上課,都去青島東路了吧!」傅心怡笑說。
「那時候我當電視組總編輯,學校當時為了保護學生和器材,怕學生以媒體身份進去有危險,便說電視組不能發太陽花議題。」她回憶當時只去過抗爭現場兩次,心怡自嘲說:「我應該是走錯團了,因為他們都是在罵中國人,可能是我一開始進去的位置比較不對吧,沒有上到街頭的課,剛好被我看到了比較恐怖的一面……」當時她見到許多從中南部翹課連夜上來的國中學生紛紛上台說自己的看法,台下就只是跟著大聲起鬨說「好!」,讓她難以苟同這種湊熱鬧的現象,「好像不是我以為民主的感覺。」
比起撤稿感想,事件經過更重要
前年底因為教育部公布「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草案,擬放寬私立大學學費調漲5%、國立大學10%,引起大學串連抗議不合理漲學費,當時傅心怡採訪世新勞權小組在舍我紀念雕像前的「我要說話:反漲學費」公聽會,為了平衡報導立場,也有去訪問校方,但直至截稿前都沒有接到回應。
原先排版的時候,這份報導被排進頭版,指導老師也讀過了,「沒想到系主任胡光夏下來看之後說那則不能放,對我來說是非常突然地被撤稿了。」當時不少人想採訪她被撤稿的感想,但因為她不是編輯並不在現場,「我沒有答應採訪的原因,是因為這些過程也是別人轉述給我的,我只能說我被撤稿的感想,但我覺得這也沒什麼好說的,他們更應該了解的是事件的經過。」
當校園報只剩藝文版,學生還能知道什麼?
畢竟世新大學是傳播界人才的重點培育基地,撤稿的爭議很快就被傳開了。後來在102學年度下學期小世界報紙組實習手冊中,原本「版面規畫」對於五版「世新最前線」的內容規畫,從「世新行政、社團等校園新聞」,改為「世新大學藝文、社團活動之校園新聞」。原本可以報導學校發生什麼事或議題,「後來變成是藝文版,就發一些可能誰今天來學校或是活動宣傳之類的。」傅心怡曾在臉書動態上感慨「只是覺得,若小世界真的不存在校園版了,或存在的只是校園藝文版(文山好鄰居版),那學生可能再也不會知道,學餐水果來源不明、舍我樓電梯分流、異便當油煙污染⋯⋯」
聊到她目前在香港衛視的實習工作,我好奇陸生無法在台打工的問題,她澄清目前實習是沒有薪水的,「原先想實習是因為以為可以因此留在台灣工作,因為香港可能是外資……,但後來發現薪水也是從台灣的戶頭匯過來的,所以我還是不能藉此留在台灣工作。」主要報導台灣的時事新聞,她笑說:「他們應該不知道我是陸生,因為我的實習身分都隱藏在臨時採訪證了,不過也還好,我也聽不到什麼國家重大的事情啦!」
在最接近牆的地方,盡最大的努力
比較兩岸在新媒體方面的發展,傅心怡認為台灣發展比較蓬勃,「在同一時間點比較,台灣的使用者比率上比較多。在大陸的閱讀資訊來源多半還是停留在官方媒體,或是門戶比較大的,比如搜狐、騰訊…..,一般民眾比較少會去看獨立媒體。」原先對台灣媒體的印象,她覺得是很開放、自由的,但後來陸續觀察到一些亂象,被撤稿事件之後也讓她體悟到媒體受到支配的一面,「被錢、被上級,或組織方面的控制,其實並沒有百分百的自由。」
另一方面她感受到自由可能帶來的亂象,「前幾天有個爸爸把自己兒子殺了,因為兒子患有疾病,兒子也同意爸爸殺了他,當時我看到新聞畫面,那個爸爸臉部已經被遮住正在押送途中,記者還在追問說『你是不是已經不再愛你兒子』之類的這種白痴問題,我就覺得還滿過分的。」為了拚命應付長官或畫面的需求,而忽略了報導過程中要注意的細節問題。「可能大家新聞做久了,反而無法感同身受。」她接著話鋒一轉,笑說自己可能也是在講風涼話,搞不好進了業界也會是如此。
因為來台灣念了四年書,雖然畢業後還沒有明確打算,但她期望之後工作地點可以離家近一點,就有比較多時間可以陪家人。目前所受到的新聞專業訓練,或是參與過的議題採訪工作,被問及是否擔心很難在中國有相當自由的發揮空間,透過這些新聞人必經的擔憂,她反省道:「你一直去撞牆、撞牆,就慢慢會知道牆的邊界在哪裡,那我就會是在最靠近牆的地方,就是在體制內盡最大的努力,因為我必須要保住我的飯碗才能一直寫下去。」
她也以之前在台灣備受討論的柴靜霧霾調查紀錄片《穹頂之下》為例,「我覺得柴靜很聰明,因為現在環保議題大家是最關心的,跟每個人息息相關,又沒有這麼威脅到政府,才會讓議題一被推出來就受到這麼多人關注,也是她在離開央視後通過獨立媒體可以發揮的影響力。」
「把自己的情感帶入報導是新聞學上的問題,但也正是因為跟受訪者感同身受,以媽媽的角色詮釋霧霾的問題,這是她向來的風格,也因此讓很多人關注這個報導。」她認為記者某方面也扮演著「意見領袖」的角色,因此有自己的觀點帶入事件很重要,未必是放進日常工作的報導中,可能是發佈在自己的平台上。「我覺得記者無論如何,一定要有自己的態度才行,不然的話,很像是這份工作在『做』你,而不是你在『做』這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