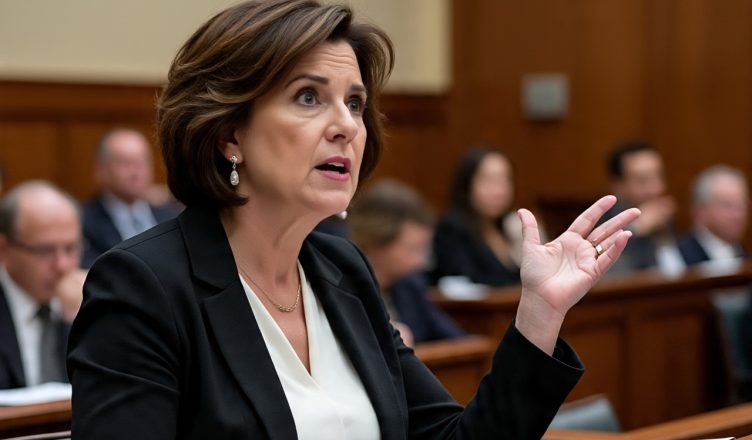文/孫靖洋 (前洛杉磯世界日報採訪主任/副總編輯)
2015年夏天,我接到陪審員徵召通知,
我參與過本案刑案部分的最前面小一段,當時我在庭上,
我參與過多次陪審員出庭待命候選,最長的是九天,
檢辯雙方在決定12位正選陪審員、2位備選陪審員之前,
那天我是最後一批被叫進法庭內,接受檢辯雙方質詢的候選人,
由於時間有點久,細節不記得,檢察官問我的問題大約是,
但在洛杉磯開車的人都知道,沒有人會在65哩的路段開65哩,
檢察官的原始動機,我能理解,很可能是在法律界定的範圍內,
檢察官提出問題後,還絮絮叨叨的講了一大篇道理,
本人的脾氣向來很火爆,在他說完最後一句後,
檢辯雙方都沒有再對我發問,但也沒有主動把我踢出去。
當天我離開法庭後,審判程序立刻展開,檢辯雙方開始開場陳詞,
我因為參與過一小段,所以也盯著新聞發展。沒想到全案審了幾天,
美國有大約八成以上 (具體數字要再查)刑事案件是以認罪協議方式結案,
但弔詭的是,那些開審之後才達成認罪協議的案子,
以該案而言,如果該田徑教練如果是清白的,
雖然很多認罪減刑的案件,有法律實務面與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考量,